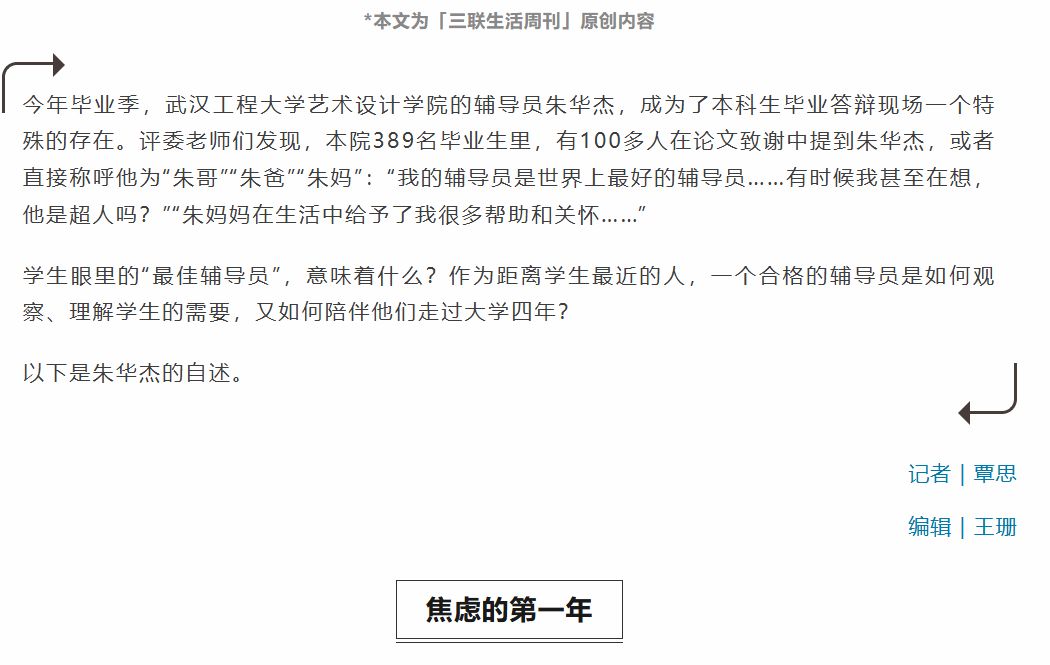
我最早是在朋友圈看到学生的致谢的,后来有几个教研室的老师过来跟我说,至少有100个学生在致谢里提到了我,我挺惊讶的。大学四年以来,我很少收到学生们这样热烈直接的表达。

朱华杰和毕业生合影(图源武汉工程大学)
我是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武汉工程大学担任辅导员的,那时我27岁。进入教育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的选择。我父亲是军人,工作调动频繁,我们总是搬家,我也就换了很多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现在想来,频繁的变动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负面影响,因为我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。
比如我初一的班主任。当时的我很贪玩,上课总偷用手机。班主任是语文老师,她把我叫去谈话,她说她很欣赏我的作文,看得出我喜欢写作,她希望我能认真学,下课再玩。那时候我的确很喜欢阅读、写东西,当我听到她点评我写的几篇作文,而且说出具体哪写得好,我才意识到她细致地观察着我。虽然一年多之后,我就离开了这个老师,但那种被看见的感觉,我一直记得。

这些可能都造就了我日后对教育的理解和兴趣:人生是分阶段的,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陪着另一个人,但在每个阶段,身边总会有一些人。如果能在一个阶段碰到某个好的老师,好的同学,我觉得就很好。在武汉体育学院读本科和硕士的几年,我几乎每个暑假都去乡村支教,来上课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,暑假缺少陪伴,但每次看到我们都笑得很开心,我也高兴自己能给他们一段“陪伴”。后来在学校,我腿受了伤,不太好再从事运动相关的工作,加上母亲身体不好,我希望留在她身边照顾。辅导员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选择。
我的第一届学生有389人,有另一位辅导员和我一起带。当时,我并不觉得学生人数特别多,我更大的压力来自对辅导员这个角色的不熟悉:上学的时候,我是那种不主动求助、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人,和辅导员接触很少。刚开始工作时,我把辅导员当作是学校通知的执行者,刻板地把所有通知一股脑发给学生,要求他们严格执行,但学生不放在心上,我的工作也吃力。
我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来安排活动。他们大一的时候,我组织了一次年级拔河比赛。我本身是体育学院毕业的,根据我的经验,拔河明显是能增强班级凝聚力的运动:大家一起使劲,一起喊口号,效果会很好。结果报名的人很少。我去问学生,他们说不想去操场,不想参加集体的运动。
我只好去找学院里更有经验的辅导员求助,他提醒我:你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,好好想一想,什么是真正跟学生有关的事?学生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?我意识到,我需要理解我的学生。
我和我的学生们相差9岁。他们是2002年左右出生的一代。我慢慢发现他们有很强的“网络属性”,他们会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情绪,这种情绪起伏又很大。他们也更习惯网上沟通,不喜欢面对面看着我的表情、对着我的脸说话。我让学生来办公室跟我聊一聊,他会说,老师我能不能不来,就打字行吗?很多学生跟我这么说。
我只能继续关注着他们在网上的动态,时不时找他们问一问,他们经常回复我千奇百怪的表情、各种各样的缩写,我就上抖音、小红书查一下什么意思。我还会认真的去看他们的朋友圈、QQ空间。一次,有个学生发朋友圈,讲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情,我去问他怎么回事。没想到他说,老师我没事,我就是在网上发疯,你不要理我。等我再一看,他竟然立刻就把我屏蔽了,我看不到他的朋友圈了。当时我就特别不能接受这个,心想我是来关心你的呀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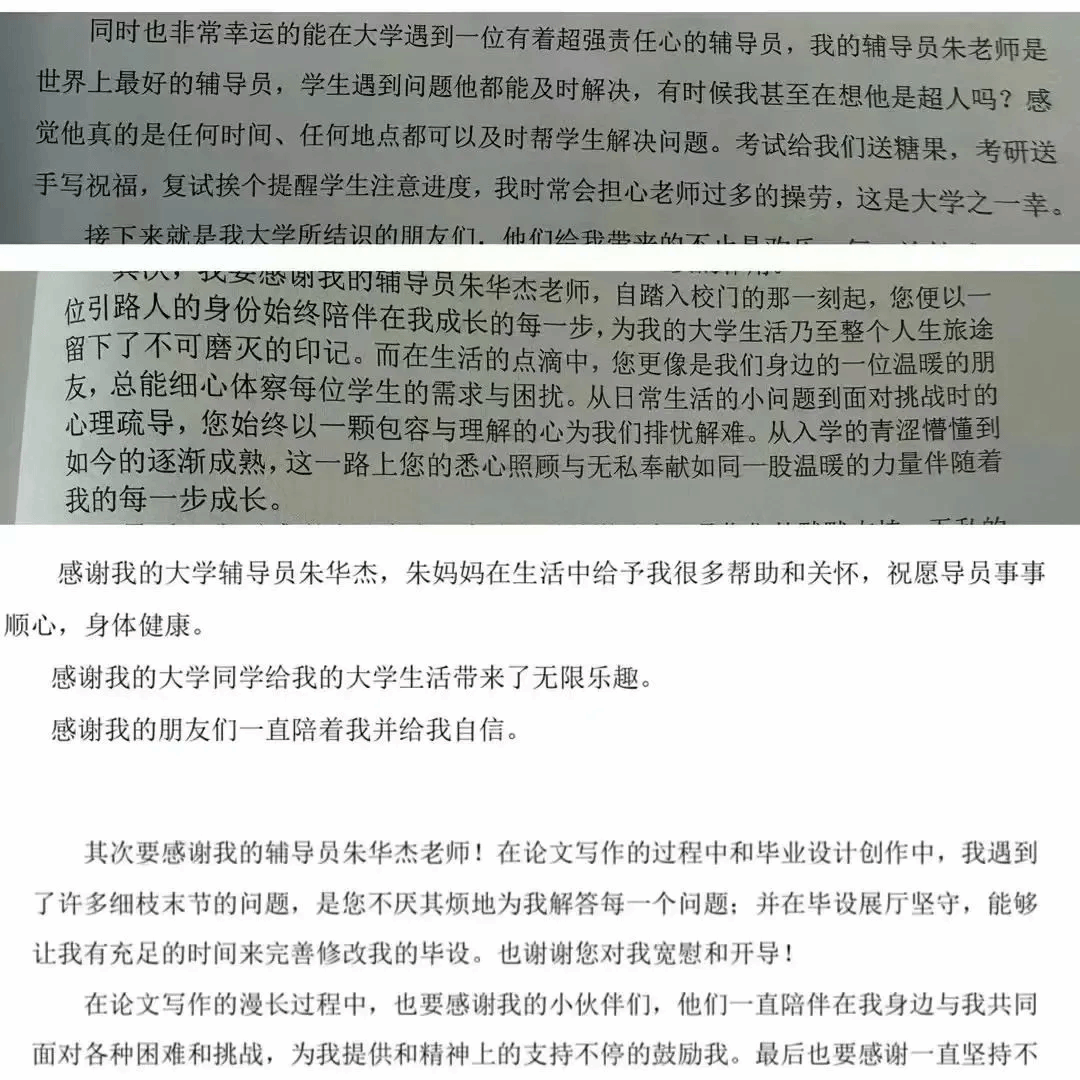
2020级毕业生在论文中致谢朱华杰(图源武汉工程大学)
可以说,当辅导员的第一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。因为我会担心,如果没法有效沟通,那学生会不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,而我没办法及时发现、帮他们解决,这种失控感让我特别难受。我感觉学生自己有一扇心门,掩得死死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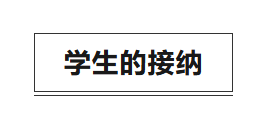
学生慢慢开始对我打开心门,还是从我陪他们度过一些困难之后。受疫情影响,在学生大一大二的时候,我常常陪同他们去医院看病,有时在医院陪护一整晚。前后有好几十个学生,就是这样熟络起来的,当他们的室友、同学遇到问题,他们会告诉对方:朱老师是一个能够沟通的老师,你去看看他能不能帮你。我会想各种办法让学生知道,我在关心他们,我和他们是同一条战线的。大二的时候,女生们面临一次宿舍搬迁。那时候正是假期,学生们都不太愿意回学校搬宿舍。我看施工的人员把新宿舍装好了,就在b 站上现场直播,给学生详细介绍寝室。1小时的直播里,学生一看就发现,噢,新宿舍确实条件好很多,反对的声音就少了一点。等正式搬的时候,我找学校物业借了几辆大的三轮车,再召集了一些男同学当志愿者,这样女生们搬宿舍的负担没那么重。

受访者供图
我很重视学生找我帮忙的请求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个“社恐”,我会想,学生来找我,他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思想斗争,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我的。比如说吴静。我最初接触到吴静,是因为她要申请国家对困难学生的助学金。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,小时候父亲受了工伤,失去劳动能力,家里很拮据。我和她聊天的时候,觉得这个孩子太礼貌了,不自信,几乎有点唯唯诺诺,跟我讲话的时候,低头、脸红,总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,即便她根本就没有犯错。比如谈到小组作业做得不够好、在奶茶店兼职的时候被客人刁难,她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。
我希望吴静能增加自信心,意识到自己不比别人差。除了口头鼓励,我邀请她来做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助管,这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岗位,每个月有工资,她协助办公室的辅导员处理一些工作。有一天,一个老师告诉我,吴静做事特别认真、任务完成的很漂亮,跟老师们的表达也很清晰。我感受到她状态的改变,能大方地跟其他人沟通了。后来她靠自己找到了实习,之后又在一家电商找到了工作,虽然还是时不时会自我怀疑,但不再那么手足无措。
学生出现好的转变,是我工作最大的意义感和动力来源,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正反馈。而且,我和学生的关系是相互启发的,学生的能量时常打动我。我记得吴静申请国家助学金的第三年,她来跟我说,她放弃今年的助学金申请,让我可以考虑其他困难的学生,因为她父亲的工伤赔偿刚刚下来了。她的善良,让我很受触动。

朱华杰带学生参加支教活动照片(图源武汉工程大学)
我相信,学生虽然因为阅历和内心的局限,可能会有脆弱、崩溃的时候,但是都有一种潜力,是能够自己走出困境的。当学生从五湖四海来到学校,脱离了父母,一下子到一个开放的空间,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我的角色就是给他们一点点支撑,也许他们就缺这一点点支撑。就像吴静,你拿一个画笔轻轻点一下,给她一个颜色,她就能放出很多很多光芒。在一些细小的时刻,我也有意让学生感受到我的存在,我会给他们发生日小红包,写一个祝福在里面。考四六级的时候,我就发棒棒糖,我说这叫幸运糖,考试有时候就需要那么一点运气。

当然,辅导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学生的思想引导,还有日常管理。那是极其琐碎的部分,比如学生不知道去哪里缴电费、去哪里考试,甚至有学生会找我替他跟任课老师沟通。我理解高中学生初入大学有一个依赖阶段,但是我会划定一个界限。比如我专门开了一个通知群,里面只有我能发消息,一个事情怎么做,我会把它分解得很清楚。学生来求助的时候,我会让学生自己先去看通知,如果看完还有问题,再来找我。学生不会跟老师沟通,我会告诉他,你在下课的时候跟上去,问老师“这个怎么弄?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导?”,这样就好了,如果尝试完还有问题,再来问我。
家长有时候想的也很简单,他就觉得有什么事,给辅导员打一个电话就好了。我接到过让我帮忙找孩子的电话,后来发现是孩子在睡觉没看手机,也有家长打来说,让我用自己的人脉帮孩子找份工作。面对无法实现的请求,我就实话实说,但我也会告诉家长,我能给他什么支持,比如我建了一个就业信息共享群,孩子会接收到这些信息,但他们也要自己努力,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。

学生给朱华杰老师送来锦旗
有一部分行政工作,我会让AI辅助我做。比如写一个报告、一个计划,我会用 AI 拟一个草稿,然后我再修改完善。我会尝试新的工具,让自己的压力降低。这些琐碎的工作,之所以能坚持下来,有个很重要的条件:学校里的每一个部门,能接住学生通过我表达的需求。我把我的位置,理解成一个巨大系统中的神经末梢。我负责把学生的问题,跟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串在一起。就拿学生搬宿舍来说,很多学生反馈说新宿舍的插座少,我就向学校后勤保障处反馈学生的诉求,申请新打一个插座,最后就实现了。
有一年暑假,宿舍楼停电,天气炎热,我向学院申请把会议室和活动室开放,把空调打开,让留校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临时过一夜。再比如有学生遇到诈骗,我就带他到保卫处,保卫处有专门的老师来帮他对接警方,我主要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。学校也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、就业指导老师等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老师,当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,我就把情况向他们反馈,同学生一起和相关的老师对接,而不是一揽子都自己做,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我们学校里有位管理层的老师说过,如果一个学生出现意外情况,这个责任不是辅导员一个人来背,是所有的学院领导、相关的职能部门一起承担这个责任。但是,如果辅导员本可通过查寝、点名、查课等多种手段了解到学生的情况,避免意外发生,但他却什么都没做,一问三不知,那么辅导员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了。一个明确的职责范围,对于辅导员来说很重要。

《开端》剧照
清晰的晋升通道,也让我能看到职业方向,能待下去。在我们学校,辅导员有双线晋升制度,可以从管理条线晋升,比如带出了优秀班集体、在辅导员竞赛中获奖,就可以加分;也可以从教师条线晋升,比如带大学生职业规划课、劳动教育课等课程,做课题、发论文,能从助教、讲师,一步一步升到副教授。这套“辅导员职业化”的制度,已经明确了。
即便有这些支持系统,说实话,辅导员依然是一个艰巨的工作。工作和生活之间,我感觉我没有平衡。我的工作时间,理论上是早上8点到办公室,下午5点半下班,不过实际上是24小时待命的,手机不能关机,万一学生有什么事情找到我,如果事情紧急,我肯定要第一时间到场处理。这几年来我没有谈恋爱,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分配时间,把工作忙完了就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一下。
工作四年下来,我感受到现在的学生们,其实和少年时的我一样,最需要的是被听见,被看见。跟学生聊天的时候,更多时候我只是听着,听他们讲很久很久。他把所有的情绪说出来之后,其实他自己就会好很多了。我的共情能力,也许来自我母亲。她是一个无条件支持我、站在我身边的人。我31岁了。不像其他同龄人的父母,她既不催婚,也不给我别的压力,只是让我做我喜欢的事,尊重我的选择。我当辅导员这几年,我母亲总跟我说,好好对待你的学生,他们好不容易考出来,然后又经历疫情,是很不容易的,你不要太严厉了,要帮他们解决困难。
(吴静为化名)